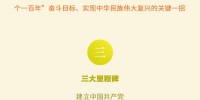【深圳商报】海南大学张志扬:幽僻处可有人行?
【深圳商报】特约撰稿 金敏华
人物档案
张志扬,1940年生于武汉,1959年肄业于华中农业学院农业机械系专业,1962年进武汉钢铁公司第三业余中学任教,1980年考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87年调进湖北大学德国哲学研究所,1994年调入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教书育人至今。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以来,张志扬属于始终既坚守学术个性又不断推进问题的少数思想者之一。其独特地位在于,在中国学术界,他既能有意识地深入跟踪不断变换的西学重述之所呈现的“古今之争”及其背后的“诸神之争”问题,又能反观中学以开启、显现与之相应的对话身份和对话能力。为此区分了“现代中国哲学”与“中国现代哲学”,并为后者应对施特劳斯新古典主义的挑战而做奠基之礼。
主要著作有《渎神的节日》、《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形而上学的巴比伦塔:下篇“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缺席的权利》、《语言空间》、《创伤记忆》、《禁止与引诱》、《偶在论》、《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一个偶在论者的觅踪:在绝对与虚无之间》、《西学中的夜行——隐匿在开端中的破裂》、《十课题书——从个人尊严的辩护到思想自由的辩护》、《幽僻处可有人行?——事件·文学·电影阅读经验》(三卷本)。
1940年生:“不忍诞辰一身墨,天公送我漫天雪。”四十年:“点苍台白露冷冷,幽僻处可有人行?”五十年:“你是世界的光,我在黑暗里走。”六十年:“知其荣守其辱,知其白守其黑。”百年苍凉:“南冥有木,彷徨乎无为其侧。”
这段话,是张志扬为自己拟的一段人物小传。
10岁解放,20岁失学,30岁坐牢,40岁入翰林,50岁南迁,天之涯,海之角……张志扬是中国哲学界真正具有原创性思想的学者。
1
对一些爱好思想的年轻人来说,张志扬的名字早就像一位秘密教父那样传开了。
说到张志扬的名字,也许有些人还很陌生,但是对于一些爱好思想的年轻人来说,张志扬的名字早就像一位秘密教父那样传开了。虽然理解或认识他的思想的人确实不多,但是凡了解了他的人无不对之深表佩服。事实上,长期未有过什么亲传弟子的张志扬,在国内不少高校内都有其崇拜者。这一有趣的现象,或许能令人想起阿伦特笔下的海德格尔。
1994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中国哲学研究》推出张志扬专辑《渎神的节日——奇异的思想历程》,刊登了米歇尔·肖恩哈尔斯博士英译的张志扬著作三章《墻》、《俑》、《X门》,并加以评价性的“编者说明”:“虽然张志扬哲学文字晦涩,但你会在字里行间发现一些真正的哲学。张志扬的晦涩难解后面所隐含的东西要比单纯的晦涩要多得多。”这也表明张志扬获得了一定的国际承认,他的思想的确值得当代中国学人关注。
要了解张志扬的哲学思想,必须从他传奇而曲折的人生经历入手。
此次出版的三卷本散文集中,第一卷《记忆中的影子回旋曲——事件阅读经验》第一次完整勾勒出张志扬的人生历程。他以1980 年进入学界作为一个大的分界线,此前四十年挑选了几个主要人生事件,此后三十年又分两段,“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和“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各挑选了若干代表性事件留下的记忆与文字。
2
一场“文革”对于我的意义,往简单里说,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我懂了何谓‘懂’。”
“我家住在长江边靠近小河口四官殿王家巷附近的民权路黄皮街小蔡家巷69 号……”在《进入“文革”的身份》一文中,张志扬描述了父亲的“历史问题”如何转移为儿子的“现实问题”,充满忏悔地回忆了个人经历的第一次大字报。他写道:
果然,“文革”前的大批判来了,如批《早春二月》,我带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其中……于是写了《文嫂之死》,发表在全国的《冶金报》上……一方面,我只是武钢三业中的代课老师,另一方面,内心已有一个声音在说:“看吧,‘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如果前述“身份”是委屈的,那么现在似乎能表明,身份下承担着的却是一颗“忠诚的心”;不管你们怎么看我,可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悟与捍卫够得上一个“自觉的战士”。
“报应”很快来了,这段经历给张志扬留下了终生的反省,他一直力图摆脱它。上世纪80年代,他在自己的学术处女作《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中,努力地、身体力行地将“批判性文字”转变为“描述性文字”,就源于这一情结。
当然不仅仅是语言观。
张志扬后来说,一场“文革”对于他的意义,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我懂了何谓‘懂’。”这对他往后走上“哲学”几乎有决定性的影响。“我既是一桩历史事件的遭遇者、承受者,又是它的幸存者、反省者,即当事人、旁观者与反省者一身三任,因此,我命里注定不能回避它。”
3
这种“守望边缘”的立场,乃是理解张志扬思想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文革”期间,张志扬因莫须有的罪名入狱七年,他在那里深刻体察了人性。对这一段经历,学者刘小枫曾如此描述:
神奇的是,张志扬在狱中开始自学哲学和德语,七年狱历等于念成哲学本科和研究生学历……莫名其妙地出狱后,张志扬被分派到一所乡村小学喂猪,一喂三年,可以算做他的博士学历——张志扬最早的哲学论文是在猪圈旁边写就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百废待兴的国家成立社科院,设考招聘研究人员,正在喂猪的张志扬凭狱中学历考得副研究员职称。我念研究生时,读到他在猪圈旁写的文思并茂的文章,感铭至深,禁不住给这位副教授写信时敬称“老师”,他却坚持自称“大哥”。
这样的经历,在当代中国学界十分罕见。
张志扬40岁时,才真正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这朵晚开的花,却结出了令人惊艳的硕果。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最先提出“存在哲学”、“语言哲学”、“政治哲学”、“创伤记忆”等哲学概念,一直暗暗引领中国哲学思潮的风起云涌。
然而,与他那秘密教父式的名声相对照的,却是他自甘边缘的位置——远在“天涯海角”的海南大学,那里几无学术氛围可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张志扬南下海南大学,与友人共同筹建海大社科中心,教书育人至今。他的低调,他对任何“中心主义话语”的警惕,在圈内人所共知。这种“守望边缘”的立场,乃是理解张志扬思想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其实,细究张志扬文字中的思想光泽,全都离不开其一脉相承的自甘“边缘”的立场,“说得形象点,我们既不想‘漂泊’也不想‘还乡’,只想把近百年的遭遇落到我们个体身上的沉重负担清算给文字——立此存照。”即使后来身处体制中,他仍然坚持着这个初衷,“不介入任何钦定的命题与头衔,清贫也罢,落寞也罢,‘民哲’也罢。”
4
“一言以蔽之”,恐怕没有比1982年他给学者赵越胜写的只有一句话的信更有代表性了:“大地、暗夜,只有脚步声。”
吉光片羽。从《记忆中的影子回旋曲——事件阅读经验》一书中,大体可感受到张志扬的两种写作风格:一类是经验性感受与描述,一类是思想性反省或沉思。
学者随笔一般被看成学者的闲余文字,张志扬的散文随笔却并非如此,而是他学术文章的补充或提供一种个案分析。其实思想随笔并不比学术论文好写,刘小枫就说过:“写小品比写学术论著费精耗神得多”,因为它是真实的“生命经历的缘分”。在此次出版的三卷本散文集中,张志扬从生存方式切入小说、电影、读书、评论、交往、沉思,逐层剥离一个人的遭遇、迷惘、破灭、反省、追问,散发着个人的生存感悟。带着问题意识的知识视野无疑更为广阔,张志扬以自己的“我思”建构着哲学的个人化风格,
最能显现他的文字风格的,或许还是脱胎于《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下篇”的《维罗纳晚祷的钟声——文学阅读经验》。在他自己看来,“《门》仍然是我最本色的文字与心态。思想、情感、意志未分地糅合在文字中,率性而为。它与(上世纪)80 年代总的文化氛围相当融洽。”
如果要“一言以蔽之”,恐怕没有比1982年他给学者赵越胜写的只有一句话的信更有代表性了:“大地、暗夜,只有脚步声。”之前在武汉,赵向他引介马勒的《悼亡儿》,张志扬如受电击。
5
我把它的严重性与“二战”后特别严重起来的“犹太人问题”相提并论,叫做“中国人问题”,即中国人如何能摆脱西方人的看而真正回复自身。
张志扬是铁杆影迷。他曾经说过,“哲学界恐怕没有谁像我这样一生都痴迷着电影的”。
他萌生过考电影学院编剧系的念头,“几乎天生地喜欢观察人,连读小说都能读得活生生地在眼前像电影样的演绎,甚至往往将自己演绎进去,如‘白日梦’”。他还写过剧本,改编了小说《保密局的枪声》,寄给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严文井导演;写过评论,“长春《电影文学》杂志发表了我的两篇电影文学评论”。不过后来认为自己“做不了影评家”,因为写起来总比别人“慢半拍”,从来赶不上趟。遂开始作不少阅读笔记,他把看电影叫读电影,像读书一样,细嚼慢咽地“品”。用他的话说,就是“我才不在乎什么技巧不技巧,一盘菜,任你是个什么做法,归根结底总要放到口中咀嚼一番,滋味总是‘咂’出来的。”于是有了这本《E弦上的咏叹调——电影阅读经验》。
张志扬的观影笔记别有况味。他在分析小说《朗读者》与电影《生死朗读》时感慨道:
上一代人不管做什么事,归根结底总要说成是为了下一代人做的。所以……“化解”至关重要。如果下一代人完全取中断的态度,即不予承担、不负责任,那么,历史就会在下一轮重复中报复地索还加倍的利息。
他最后在《电影中的“凝视”引导》这一节中,如此总结:
为什么“看”被固执于一种“定向地看”?怎样能够打破这种“固执看”的固执?最后,“如何看”才是“看”应有的敞开与关怀?……回答上述问题,几乎成为中国170 年来的灾难史。我把它的严重性与“二战”后特别严重起来的“犹太人问题”相提并论,叫做“中国人问题”,即中国人如何能摆脱西方人的看而真正回复自身。
他的电影阅读体验仿佛在等待有心的邂逅者的会饮。而电影对他真正的意义或许在于,“正是看电影,包括看画听音乐,包括喝茶喝咖啡,所有这些我都拿到同等重要的气定神闲中来,即便比例的时间少得可怜,10比1如何,它也是我血液中软化动脉的微量元素,我的文字生命才没有干瘪,没有枯槁,没有提前‘墓木拱矣’。”
他最先提出“存在哲学”、“语言哲学”、“政治哲学”、“创伤记忆”等哲学概念,一直暗暗引领中国哲学思潮的风起云涌,他的名字,却因其“自甘边缘”的立场而少有人知。
学者随笔一般被看成闲余文字,张志扬的散文却并非如此,而是他学术系统的一种补充。他新近出版的三卷本散文集《幽僻处可有人行?——事件·文学·电影阅读经验》呈现了这位自嘲为“民哲”(编者注:相对“官哲”的一个说法,指的是民间哲学研究者)的思想家的另一面:他传奇而曲折的生命历程,重要的人生“事件”,他的小说、艺术和电影的私家记忆……其中幽微难言的思绪、千磨万击的自我拷问摄人心魄,正所谓“点苍台白露冷冷,幽僻处可有人行?”